
2021年12月14日晚上19:00,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付亮老师应“三台史学”讲坛系列讲座邀请,于线上举办了题为“‘复数的’、‘全球的’宗教改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台州学院历史学系程利伟老师主持,共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师生近两百余人参与此次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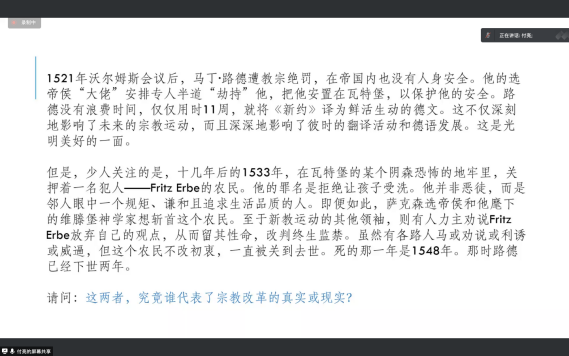
讲座伊始,付老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志业,并以1521年沃尔姆斯会议后暂居瓦特堡的马丁·路德和1533年关押在瓦特堡地牢里的农民Fritz Erbe的故事引出讲座的内容。两则故事中的主人翁路德和Fritz Erbe到底谁代表了宗教改革的真实、谁又能被建构为宗教改革的“解释”呢?付老师指出:“发生了什么,远没有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重要”(What happened is less important than what people think happened.)。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解释与书写;就宗教史而言,政治目的、意识形态与教派利益构建了“后设解释框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宗教改革史书写即是一例。大体而言,学界对宗教改革史的研究受三大“幽灵”——“黑格尔的幽灵”、“兰克的幽灵”和“韦伯的幽灵”——的影响,认为宗教改革代表进步与现代性。例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认为是“天主教会的腐败导致了宗教改革。这种腐败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天主教会在权力和统治上的全面溃败”;“宗教改革的本质是人在他的真正本质上是注定要获取解放和自由”。兰克在《教皇史》中指出:“新教是基督宗教中的最高级模式,是最合适的、而且是注定要成为近现代日耳曼民族的宗教”。兰克的这种观点构成了“新教沙文主义”的根基,兰克及其学生以及受兰克影响的学者把这个根基奉为德国历史书写的信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解释道: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最根本元素是基督教的禁欲苦修或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精神,而加尔文宗则体现了这种精神。但韦伯恐怕没有注意到,早于路德或与路德同时代的天主教人士,其中不乏在此间尘世努力工作或追求现世成功之人;他们同时认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过修道生活,也不应该要求人人过禁欲苦修的生活。在尘世中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荣耀上主。只不过,随着16世纪中期天主教会路线斗争的加剧,持此种观点的人士遭受严重打击,天主教会亦逐渐走向自我革新的单一路线。由此,付老师认为“宗教改革的故事需要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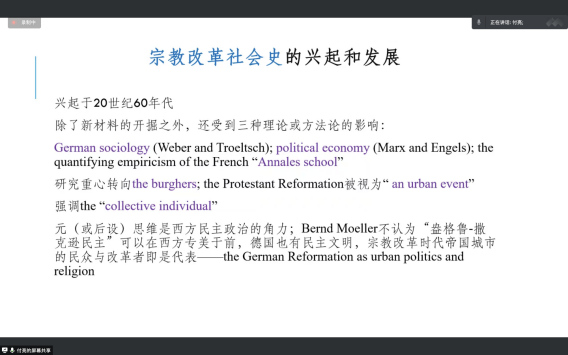
接着,付老师指出,自20世纪中叶起,在一些带有的教派倾向的作品中就开始出现对宗教改革故事的修正,将宗教改革纳入广义的宗教史而非狭义的神学研究范畴。譬如:美国学者Roland H. Bainton的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以及英国学者E. Gordon Rupp的Luther’s Progress to the Diet of Worms与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Luther Studies。20世纪60年代,(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开始摆脱僵化的神学教义研究模式,例如名史家Bernd Moeller提出了“城市的”宗教改革、“市民的”宗教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宗教改革史学史亦受到重视。例如,A. G. Dickens 和 John Tonkin主编的The Re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s就系统梳理了宗教改革的史学发展脉络。1990年,欧美两个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史研究协会合作,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参会的39篇论文基本是欧美各占一半,反映出宗教改革史研究朝更加客观、更加细致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转向呢?付老师分析道,主要是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宗教改革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的影响。当时有三种理论——Weber和 Troeltsch的德国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可量化的实验主义——影响着宗教改革史的研究,并推动研究重心转向市民,并关注德意志地区之外的伦敦、巴黎等城市的宗教改革,将新教改革视为“一种城市事件(an urban event)”,强调“集体的个体(collective individual)”。在这场研究转向的过程中,也隐含着一种元(或后设)思维。受到西方民主政治角力的影响,Bernd Moeller不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可以在西方专美于前,德国也有民主文明,宗教改革时代帝国城市的民众与改革者即是代表。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德国流亡历史学家Hans Baron就在《英国历史评论》发表了《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帝国城市的宗教与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German Imperial Cities during the Reformation)一文,其远见卓识甚至早于Moeller。
受Bernd Moeller的影响,学者们开始研究Zurich、Nuremberg、Strasbourg、Erfurt、Colmar、Basel、Augsburg、Heilbronn等城市的宗教与社会问题,涉及的议题包括市议会中的市政官员、行会中的市民、街道上或教堂中的普通人以及讲道台上的布道者,这些议题渐成为研究上的“范型”。1978年,欧美的宗教社会史学者在伦敦开会,交流对宗教改革时期市民和贵族的历史作用的看法。实际上,“市民的宗教改革”彼时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历史选题。此时,德国地区的学者对贵族的角色则更为在意。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宗教改革社会史演技欧蓬勃发展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东德学者所关注的宗教改革中的农民战争或农民阶级议题反而变得“黯然失色”了。例如在1978年的伦敦会议上,农民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并没有被与会学者关注。实际上,对德国农民战争与农民本身的研究是德语地区更为关注的选题,在英语学界则缺少重视,甚至在1980年代一度成为失语的状态。不过,少数英美学者仍然做出了贡献,譬如苏格兰史家Tom Scott、澳大利亚出生的当时英语学界最优秀的宗教改革史家Robert W. Scribner。Tom Scott挑战了Peter Blickle的观点。Peter Blickle认为,农民与市民分享的公社生活理念是普通人追求政治梦想的根基。Tom Scott则认为两造的联盟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不管如何,宗教改革社会史的研究还是做到了选题的拓展,比如普通人的各种历史和牧师阶层的社会史研究。
同时,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还深入激发学界更加关注“再洗礼派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Anabaptism)。其实,提到再洗礼派(或曰重洗派)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及美国门诺派学者Harold S. Bender。他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为学界提出了一条研究取径。他心目中的“标准化的再洗礼派(normative Anabaptism)”源自“瑞士兄弟会(Swiss Brethren)”,而非明斯特城的“再洗礼王国”。到1962年,美国一位论派学者、哈佛神学院教授George Huntston Williams将那些“非主流”新教人士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释为“极端的宗教改革运动” (the Radical Reformation)。不过,随着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上述两位学者划定的标准也遭到挑战和修正。有学者认为再洗礼派遭受的打击被严重夸大了,其中不少人回到了主流路线。另有学者认为,并没有所谓“标准的再洗礼派”,实则有多种再洗礼派群体与多种相关的历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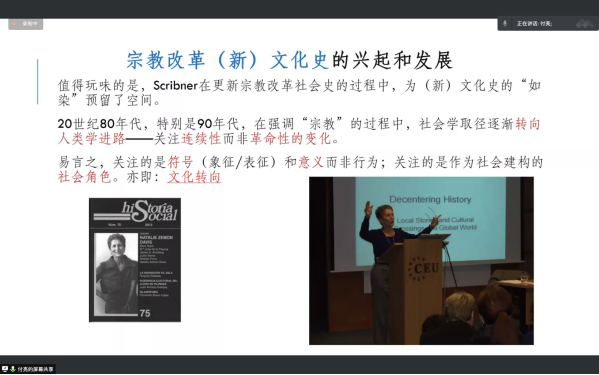
随后,付老师阐述道,宗教改革文化史的研究进路实际上也是从宗教改革社会史内部生发出来的。它肇始于对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中期,批评就已出现,譬如Bob Scribner。他在研究科隆这个城市的时候,开始思考以往的做法是否可行,因为这个地方的坚定的天主教信仰让传统的社会史进路无法有效地因应问题。在他于1977年发表了《是否存在宗教改革社会史?》(Is Ther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一文之后,Bob Scribner开始转向普通人的宗教信仰史研究。普通人的宗教信仰让他发现了斯时世界的一种心态或心理上的“范型”:多种权力与保护物(譬如护身符)搭建的网络,可以让普通人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借由研究天主教,Bob Scribner创设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考量新教徒创新的一面和压迫的一面——“尘世的神圣观”与“形式化的重复的仪礼”。因为在他看来,宗教实则是文化核心、核心价值观与动机的承载物以及转向行动的情感刺激,所以要更新对宗教改革的理解,要对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进行“系统升级”。同时,Bob Scribner也批评了Peter Blickle的学说。Peter Blickle认为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植根于公社传统习俗与价值观的革命运动,追求的是按公社模式搭建起来的乡村与城镇所追求的正义和所谓兄弟情谊。然而,Bob Scribner则指出,这种观点将宗教(信仰)边缘化,从而夸大了公社主义(或曰公有主义)理念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在实际运用中的特质。值得玩味的是,Bob Scribner在更新宗教改革社会史的过程中,为(新)文化史的“如染”预留了空间。
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起,在强调“宗教”的过程中,社会学取径逐渐转向人类学进路——关注连续性而非革命性的变化。易言之,关注的是符号(象征/表征)和意义,而非行为;关注的是作为社会建构的社会角色,亦即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尤其体现在女性与性别关系建构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晚期,宗教改革对女性在性别关系建构中施加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女性宗教改革”。譬如,牛津大学历史学家Lyndal Roper对奥格斯堡女性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地位身份等变化的研究:修女院遭强行关闭,新的属灵空间被强制放在男性主宰的家庭。传统观点认为,在“父亲主导”的时代,父权制(或曰男权制)是性别关系的自然且进步的形式;解散修道院、废除教会的独身制度,对女性意味着解放。但是,Lyndal Roper的研究认为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女性并未被解放,当时的欧洲女性在修道院要比在家庭生活中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文化史并非为了取代,实则也没有取代宗教改革社会史,而是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并补充后者、丰富后者,甚至与后者相融。譬如,宗教改革社会史在处理善与恶、生命与死亡、家庭与邻里等等“活生生的宗教”问题上并不得力。德国著名宗教改革文化史家Ulinka Rublack离开德国投身剑桥大学后,在其英文再版的《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一书中用更细腻的手法挑战了德国“传统的”宗教改革史研究中“革命”、“进步”与“现代性”的观点。与Ulinka Rublack一样,Ute Lotz-Heumann也不满意德国的“传统的”宗教改革史研究路数,而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发展。她目前以文化史的方法,探析近代早期德国的“SPA”(水疗)的被迫“教派化”及其与社会、文化、记忆、认同等方面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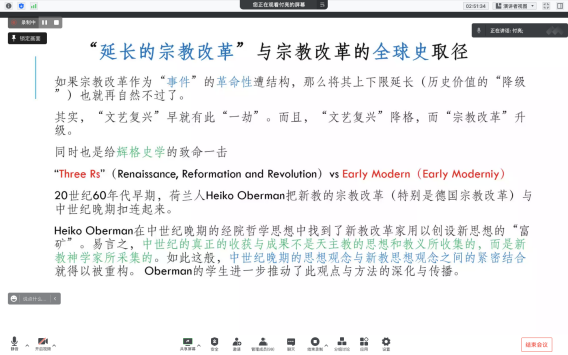
讲座最后,付老师解释了“延长的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全球史取径问题。就“延长的宗教改革”而言,他指出:“如果宗教改革作为“事件”的革命性遭结构,那么将其上下限延长(历史价值的“降级”)也就再自然不过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荷兰人Heiko Oberman把新教的宗教改革(特别是德国宗教改革)与中世纪晚期扣连起来。Heiko Oberman在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思想中找到了新教改革家用以创设新思想的“富矿”。易言之,中世纪的真正的收获与成果,不是天主教的思想和教义所收集的,而是新教神学家所采集的。如此这般,中世纪晚期的思想观念与新教思想观念之间的紧密结合就得以被重构。Oberman的学生进一步推动了此观点与方法的深化与传播。到20世纪80年代,“教派化”命题的研究也出现了对“革命性”的解构。该命题认为宗教改革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1546年路德去世后的100年,这一百年乃是教派建立的时代。此后,教会和国家联手将宗教、社会、性、甚至是政治规训作为一种建立民族国家、建立专制主义的工具,使民众为政治、社会和文化向现代性的转变做好准备。在此时,三大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后特兰托时代”的罗马天主教——处于一种平行发展的态势,因为它们都指向近代性(或曰现代性),也就是它们寻求近代性或现代性的长时段。一些学者甚至将此命题用于研究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与地区。“教派化”命题的目标,就是“埋葬”宗教改革作为革命的论点。它恰恰是一个“反论题”(counter-thesis),由此造成的代价是“我们失去了‘单数的(传统的)’宗教改革”。
就宗教改革的全球史取径来说,付老师认为,研究近代早期的学者往往都是全球史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因为这个时代是大航海的时代、文化互动的时代,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拓殖的时代,同时也是天主教、新教诸宗等在全世界散布、变形的时代。欧洲与世界上的各个地区纠缠在一起,此时,宗教改革作为一种“突变的”、“革命的”事件或者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教义的改革的意义已经不大,实际上应该将其看成“全球的”动态过程。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审视宗教改革:它生发于欧洲,植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当中;它的驱动力是基督教各宗派;但客观上,无法预料的 “多运动构成的整体运动”,外溢到了整个世界当中,又与其他文化、民族、宗教产生了难以预料的、丰富的、多元的互动。这就是所谓的“全球的”宗教改革。

在讲座过程中,付老师还推荐了一些适合本科生阅读的宗教改革史的书籍,例如:Thomas A. Brady、Heiko A. Oberman与James D. Tracy主编的Handbook of European history, 1400-1600;H. J. Hillerbrand主编的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n;Ulinka Rublack的Reformation Europe: New Approaches To European History;Nichols Terpstra的Global Reformations Sourcebook等等。
讲座尾声,与会师生踊跃提问,涉及到“印刷术、图像、声音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史学史”、“教派的自我塑造”,付老师进行了细致的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讲座让同学不仅对宗教改革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将来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